
《辛德勒的名单》剧照
“看见了吗?”瘦到皮包骨头的可怜人带着扭曲的笑容,透过墙上的缝隙,指着烟囱里冒出的滚滚浓烟自言自语道,“那就是你们亲人所在的地方,那也是我们都会去的地方!”
“美丽的女士,你怀孕了吗?”当佩莉斯嘉·勒文拜诺娃被问到这个问题时,那位党卫队讯问者面带微笑,双腿叉开站在她面前,像法医检验尸体那样对她上下打量。
约瑟夫·门格勒医生站定在这位28岁的斯洛伐克女教师面前,她一丝不挂地站在露天操场上,因为羞愧难当而瑟瑟发抖。就在几个小时前,她来到奥斯维辛二号营——比克瑙。时间是1944年10月。
在可怕的混乱中,佩莉斯嘉来到三个巨型集体灭绝营中的二号营,这三个灭绝营被统称为奥斯维辛。
刚刚从斯洛伐克抵达的人们惨遭猎犬撕咬,而被称为“牢头”、身穿条纹囚服的囚犯头目则对人们肆意叫骂,粗暴地把人们从车厢里拽下来。冷酷无情的党卫队哨兵手持武器站在旁边。佩莉斯嘉说:“我们过去甚至不知道何谓奥斯维辛,但从跳下火车那刻起,我们就都知道了。”
人们被这个超现实世界——通上高压电的带刺铁丝网、瞭望塔上配备机关枪的士兵、横扫夜空的探照灯光——吓得目瞪口呆,佩莉斯嘉和丈夫蒂博尔也立即感受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敌意和攻击,周围传来皮鞭挥舞的响声,有人对他们大喊大叫:“滚出来!快!扔掉行李!快!”

△通上高压电的带刺铁丝网、瞭望塔上配备机关枪的士兵、横扫夜空的探照灯光 资料图
男女老幼同样无助,人们被赶下火车,随即被推入人群中。人们在混乱中跌跌撞撞,很快就被冲散,珍贵的手提箱也被弃置在泥泞的水洼里。有些妇女变得歇斯底里,她们试图抓住亲人或护住孩子,却被充满敌意的陌生人强行推开。
佩莉斯嘉想要抓住丈夫的手臂,却被强行推开,几乎跌倒在地,幸好埃迪塔设法扶住她。佩莉斯嘉哭了,她绝望地四处张望,却再也未能看见她那年轻丈夫的身影,蒂博尔早就被周围拥挤的人群所吞没。
佩莉斯嘉蹒跚前行时,突然与一名党卫队高级军官打了个照面,她后来才知道此人名叫门格勒。在当时,对于佩莉斯嘉来说,此人只不过是另一名眼神冷峻的纳粹军官而已。
门格勒带着似乎永远镶嵌在脸上的笑容问道:“需要帮忙吗,美丽的女士?”
佩莉斯嘉站直身体,抬起下巴,轻蔑地回答道:“在这里,不需要。”
门格勒命令道:“给我看看你的牙齿。”
佩莉斯嘉犹豫片刻,还是张开了嘴巴。
门格勒斩钉截铁地命令道:“干活去!”
许多粗暴的手把她推向右边的行列。她发觉自己淹没在痛苦的人海中,谁都不能站立或回头。蒂博尔已经消失在几百米开外的混乱人潮中,她甚至无法确定埃迪塔是否能够跟上她。
牢头和穿着制服的党卫队看守挥动棍棒,大喊“快点!”他们命令妇女们每五人一行,肩并肩地通过泥泞不堪的走廊,走廊两边分别是深陷的沟渠和高耸的带刺铁丝网。妇女们被带到营区外围一栋偏僻的砖砌楼房,被塞进一处装有窗户的狭长房间,随即又被要求脱光衣服,以便进行“消毒”。
许多妇女感到震惊,因为即使在丈夫面前,她们也从未全身赤裸任人打量,她们犹豫不决。稍有迟疑,或者乞求以衣服覆盖身体,她们就会遭到殴打,直至乖乖从命。妇女们脱下或摘下的衣服、手表、钞票、珠宝堆积如山,随后被送到奥斯维辛的商业中心进行分类,在那里,每次大约有1000名犹太女囚犯脱去衣服,她们脱下来的衣服可以堆到三层楼高。
一旦新来者被脱光衣服,她们就会沿着走廊被赶进一处小房间。在那里,会有人熟练地检查她们的口腔以及其他孔洞,以搜寻藏匿的黄金或宝石。那些害怕失去一切的妇女,早已让牙医在补牙材料里填上钻石。有些妇女则把珠宝藏在阴道里。绝大多数黄金宝石都会被找到。一旦通过检查,妇女们就会像绵羊被剪羊毛一样,由理发师借助手动或电动理发剪匆匆忙忙地剃去所有毛发。
妇女们低头饮泣,她们宝贵的头发,曾经如此细心呵护和烫染的头发,现在却被剃去,被装进麻袋。剃去毛发,被视为让妇女们迅速认清自己身为囚犯的措施,也是为了降低被虱子叮咬的风险。以半钝的剃刀剃去毛发,成为最具有冲击力的步骤,让这些身陷囹圄的斯洛伐克妇女丧失人格。
被剥夺衣服、毛发、身份、尊严后,她们通常已伤痕累累,她们的头皮被剃得乱七八糟,只留下几寸长的杂乱毛发,朋友和亲人挤在一起、抱在一起,害怕彼此分开,因为她们突然看上去千人一面,已经“不再是人类了”。
由于有太多妇女在楼房里接受深入检查,妇女们被迫在大操场上等待初次点名,以及由比克瑙妇女营主任医师门格勒主持的再次检查。寒冷刺骨的空气向她们赤裸的头部和身体袭来,让她们气喘吁吁。她们不能东张西望,只能每五人一组接受仔细检查。她们畏畏缩缩地站在泥泞中,感觉到整个世界已经倾颓,一度熟悉的生活已被永远剥夺。
随着门格勒医生走近,佩莉斯嘉看见医生把面带病容、身上带有明显伤疤或伤口的妇女拉出队列。有时候,医生似乎仅仅由于厌恶某人的面容就把某人拉出队列。佩莉斯嘉偷听到医生对前面几位女囚犯的提问,知道会被问及是否怀孕。尽管她在外表上凛然不可侵犯,但内心从未感到如此屈辱和害怕。
然后,医生突然站到她面前,面带笑容,靠得如此之近,以至于她能够闻到对方脸上那刮完胡子后涂抹的爽肤水的味道。她昂起了头。与那身体面帅气的制服极不相称,门格勒满是欣赏地对她上下打量,似乎对她那健美的躯体留下了深刻印象。相比之下,她周围那些妇女简直是骨瘦如柴,许多妇女瘦得只剩皮包骨头,还满身疥疮。
佩莉斯嘉知道,绝对不能信任这名医生。如果希特勒真的打算说到做到,在欧洲清除所有犹太人,那么这肯定意味着,就连犹太人尚未降生的孩子也将难以幸免。
在门格勒目不转睛地研究她的躯体时,她只有几秒钟时间做决定。但在门格勒以德语问她是否怀孕后的几秒钟里,佩莉斯嘉直视前方,与对手正面对望。
佩莉斯嘉用德语回答道:“没有。”她不愿承认她懂得医生及其同党引以为傲的这门语言。她的心脏在胸口剧烈地跳动。她知道如果暴露怀孕的事实,后果将极其严重。尽管迟疑了片刻,但这名带有人类学博士头衔、一心想成为伟大科学家的医生还是冷漠地走了过去,走向队列里的下一位妇女。
一旦通过初次点名,佩莉斯嘉以及其他妇女就被驱赶回崭新的盥洗室。这座盥洗室有许多窗户,呈现“T”形布局,是为少数被分配到工作的囚犯而设计的。她们仍然赤身裸体,被带到一座混凝土结构的淋浴房。在那里,牢头做着卑鄙的手势,说着下流的脏话,以此向在头顶上监视的主子拍马屁。妇女们满身疲倦地站在复杂的网格铜管以及巨大的金属喷头下。她们成群结队地赤脚站立在光滑的地板上,这种等待简直是折磨。
突然之间,热气腾腾的水流从头顶上倾泻而下,妇女们因为震惊和恐惧而尖叫。她们扬起头、张开口,试图缓解口渴,但比克瑙的水并不适宜饮用,她们很快就吐出口中咸得发苦的脏水。牢头向妇女们的头上和腋下喷洒让人刺痛的消毒剂,消毒剂让她们的伤疤或伤口更加刺痛。
她们才洗湿身体,就被不断叫嚷的看守驱赶到另一个房间,她们只有几分钟时间来擦干身体。她们沿着与入口处平行的另一条走廊前进,被带到与脱衣室同样巨大的另一个厅堂,然后被塞进厅堂边上一间没有门的公共厕所。
妇女们被迫每五人一组蹲在地面的茅坑上,她们被茅坑里升腾起来的恶臭熏得难受。由于不停地被棍棒猛戳,而且那里没有手纸,只有极少数人在被赶出茅坑之前能够完事。在害怕与困惑中,她们被带进大厅外围的另一个小房间,那里有堆积如山的破衣烂衫。每一名妇女走进去的时候,那里的狱友就随手扔给她一两件破烂衣服。
由于发放者与领受者没有任何眼神接触,那几双脏手扔过来的衣服也是张冠李戴到荒唐可笑,而发放者的选择也意味着生与死的差别。佩莉斯嘉在胡乱堆放的鞋子里拿到裹脚之物,还拿到一件用料厚实、宽松垂坠的女式大衣,对此她非常感激。许多没那么幸运的同伴只拿到不合身的衣服,比如太过窄小的衣服、男性内衣裤甚至缎面睡衣。如果在别的地方,这种衣不称身的场景肯定引人发笑。然而,当她们把滑稽的囚服套在潮湿的皮肤上并且彼此审视时,她们都有越发严重的不祥预感。
佩莉斯嘉初到奥斯维辛二号营——比克瑙,还不知道这里发生的任何事情。她能够感觉到的是,她被关在缺少空气、没有窗户的棚屋中,屋里挤进了太多人,这对于她和未出生的孩子来说都是极度危险的。不幸中之万幸,她与朋友埃迪塔重逢了,从此再未分开。
只有当街区里的妇女们在黑暗中窃窃私语时,佩莉斯嘉才领会到何谓死亡。来自不同国家的老囚犯头发掉光、眼窝深陷,她们会偷偷挨近新来者,问对方身上是否还有食物。在得到失望的回答后,她们就开始告诉新来者,营区内会发生什么事情,并且开始互相争吵。
她们就是来这里受死的,要么累死,要么饿死,她们注定毫无希望。不,另一个人坚持说,她们只是被隔离,人们开始争吵内讧。为什么那么多人都被剪了头发,只有少数人被打上烙印?第三个人解释说,她们都应该祈祷,祈求被选入劳动营,因为这是她们生还的唯一希望。
但其他人在哪儿呢?新来者伤心地问道。家人现在如何呢?家人住在其他营房,还是被送到其他地方劳动呢?
“看见了吗?”瘦到皮包骨头的可怜人带着扭曲的笑容,透过墙上的缝隙,指着烟囱里冒出的滚滚浓烟自言自语道,“那就是你们亲人所在的地方,那也是我们都会去的地方!”
焚烧死尸的浓烟笼罩在她们周围。佩莉斯嘉说:“每天发生的事情都非常清晰地告诉我们,妇女以及尚在孕育中的孩子会遭逢什么命运。逻辑告诉我,在这人间地狱,存活下来的机会微乎其微。”
在这个令人丧失信仰的地方,佩莉斯嘉所信奉的一切就是千方百计地保住孩子,这就意味着不能像其他人那样活活饿死。人们很快就发现,她们赖以生存的所有食物都是清汤寡水,也就是德国人称为咖啡的“洗碗水”,用沼泽地的脏水和烧过的小麦熬制而成,她们早饭晚饭都吃这种东西。正午时分则是用烂菜叶熬成的难以形容的汤,里面漂浮着她们仅有的固体食物,一小片发黑的掺了锯木屑的面包。吃着这种东西,让佩莉斯嘉在清晨发生妊娠反应时吐无可吐。
出于动物的求生本能,佩莉斯嘉和埃迪塔发现,其他狱友会在黑暗中惊醒,在其他囚犯把汤送进来的一刻,猛然冲向那个容积只有50夸脱的汤桶。争吵马上在不同圈子、不同国籍的囚犯之间爆发,牢头马上抄起棍棒或胶管,狠狠惩罚那些跪在地上舔食汤汁的人,或者像豺狼虎豹那样狠狠教训每个不听号令的人。
那些最饥饿的人,忍受着雨点般的棍棒敲打,像鱼儿一样围到汤桶边上,伸出肮脏的双手,想要捞点足以果腹的东西。每一小块汤渣都可能让她们存活下来,过去习以为常的洗手礼仪早已抛诸脑后。佩莉斯嘉看到,最好是沿着桶底的边缘刮上一满勺,不过,人人都想这样,人人都得排队。
当把她们从不清洗的碗舔干净,当仅有的、足以致盲的探照灯光划破营区的夜空,佩莉斯嘉以及狱友们就可以睡上六个多小时了。她们躺在简陋的木板床上,营房没有窗户,却有很多漏风漏雨的缝隙。她们躺在薄薄的床垫或肮脏的草垫上,几个人盖一床薄薄的被单。她们整个晚上都穿着鞋子或靴子,以免被人偷走,她们紧紧抱着弥足珍贵的碗或勺子,就像抱着救生筏子。
 △无论妇女们睡在哪一层,她们都会因为腰酸背痛而难以入眠。 资料图
△无论妇女们睡在哪一层,她们都会因为腰酸背痛而难以入眠。 资料图
那些睡在三层架子床下铺的人最为幸运,但她们还是会遭到老鼠的骚扰,老鼠在潮湿的地面上窜来窜去,啃食人们脚上的死皮。那些睡在中铺的人在夏天的几个月要忍受炎热和缺氧之苦,而那些睡在上铺的人,夏天热如火烤,冬天冷如水泡,不过至少还能舔食冰雪或雨水。无论妇女们睡在哪一层,她们都会因为腰酸背痛而难以入眠。
人们无事可做、无事可想,只剩下恐惧、饥饿以及难忍的口渴,佩莉斯嘉以及其他囚犯害怕时间流逝,她们焦虑地等待自己的最终命运。
所有妇女都在牢头的监视之下。这些牢头要么是职业罪犯,靠作奸犯科赢得他们的特权地位,要么已经证明自己能够胜任纳粹指使的任何残忍行为。有些囚犯在奥斯维辛待了好几年,早就知道要想活得更久,就得模仿主人的残暴行径。与纳粹体制下的所有监狱走卒一样,他们的任期取决于他们能否胜任。如果太过仁慈,他们就可能受到严厉惩罚,甚至迅速被送进毒气室;如果反感党卫队的所作所为,他们就会被剥夺职衔,并被投入他们看管过的营房,通常很快就会被他们折磨过的人弄死。
就是这样,牢头帮助维持秩序,尤其是在党卫队员离开营区的晚上。作为回报,他们会分配到主营房以外的房间,那里有更好的床铺和食物。也能得到在冬季取暖的燃料。那些在他们监管下的妇女必须服服帖帖,否则就会遭到殴打,而极少数反抗分子的下场还要更惨。
尽管如此,到了晚上,囚犯们还是会用各种语言窃窃私语,谈论朋友、家庭、丈夫、爱人、孩子以及她们失散的亲人。对孩子、父母、丈夫的思念折磨着她们。她们渴望看到色彩斑斓的世界,渴望听到欢声笑语、鸟叫虫鸣,渴望看到鲜花。偶尔,她们还会背诵诗篇,或者复述书本中最喜欢的段落。如果足够大胆,她们还会低声合唱,经常会有人因为这些低吟浅唱或感人挽歌而潸然泪下。
不过,人们谈论得最多的还是食物。就在这散发着难闻气味的角落里,她们回想起家里的厨房,那里弥漫着出炉面包的芳香,饭桌上摆满食物,还有甜美的红酒。
当她们身心俱疲时,就彼此紧靠在一起,以至于动弹不得。就连党卫队的狗舍都比她们的营房宽敞。她们手肘贴着手肘比邻而卧,如果一位妇女想要转身,放松一下被木头硌得生疼的髋骨,或者爬下床铺使用尿桶,所有妇女都会被弄醒。她们尴尬而断续的睡眠还会被噩梦、自然界发出的声响以及关于家庭的心碎梦境所打断。
每天清晨4点左右,妇女们就会被刺耳的铃声或铜锣声粗暴地惊醒,还会有人冲着她们大喊大叫,敲打她们的双脚,女牢头来回走动,把她们赶下床铺去点名,她们会被反反复复地清点。探照灯光让她们头昏目眩,泥泞地面让她们站立不稳,她们被迫每五个人站成一排,在指定的点名区域站上十二个小时。无论天气如何恶劣,都得接受清点。那些独木难支的囚犯得靠朋友扶着,因为任何人牙口不好、身上带伤或虚弱到难以站立,都必定难逃一死。
妇女们只能用口呼吸,以免闻到阵阵袭来的尸体臭味,她们经常在刮过原野的刺骨寒风以及冰冷雨雪中裸身站立。门格勒以其作为医生的专业眼光,决定她们当天受死,或者在工厂里为第三帝国劳累而死。他对这份工作如此热诚,就连他不当班的时间也照常出现并进行这种筛选。
有一天,佩莉斯嘉被吓坏了,门格勒径直向她走来,粗暴地挤压她的乳房。佩莉斯嘉说:“我当时非常害怕,如果被挤出奶水就糟了,上帝保佑,我躲过去了。”门格勒以他淡褐色的眼睛紧盯着佩莉斯嘉,这个医生曾经在乌克兰战役期间因为类似行径而获得一枚铁十字勋章,此时他对佩莉斯嘉审视片刻,然后就走开了。
另一位女囚犯的乳房也受到类似的挤压,当门格勒高声喊出“有奶水!怀孕了!”时,她被吓坏了。门格勒就像在舞台左侧调度演员的导演,轻轻一挥手,那位女囚犯就乖乖出列,被指派到一名女性驻营医生那儿,医生粗略检查过后就说她怀孕了。女囚犯极力否认,但女医生坚持己见,当女医生去找看守时,那位女囚犯抓住机会逃跑了,跑回正在点名的人群中,此举救回了她的性命。
就算是门格勒也是要睡觉的;其他医生同样如此,其中就包括弗里茨·克莱因医生,他总是带着几条军犬巡逻,一副居高临下的表情,他也负责某些清晨的筛选行动。他首先询问妇女的姓名、年龄、国籍,检查她们身上是否有湿疹、伤痕、畸形,然后动动手指,示意这些妇女是可以侥幸活过这天,还是马上被送去毒气室。
 △一位母亲和她的孩子们步行到毒气室。 资料图
△一位母亲和她的孩子们步行到毒气室。 资料图
每到傍晚,妇女们就要经历同样的致命程序,她们的生命会被再次估价。那些放弃生命的囚犯,那些因为腹泻、疾病、脱水而无法站直的囚犯,都会被带走,她们几乎不可能再出现在众人面前。
埃迪塔还在悉心照顾她那怀孕的伙伴,帮她站直,睡她旁边,给她保护和温暖。偶尔,且总是在晚上,埃迪塔会在佩莉斯嘉耳边轻声地说:“张开嘴巴。”佩莉斯嘉照做,奇迹般地,一小片生土豆或一小片黑面包,就会塞进她颤抖的牙缝中。“这是我吃过的最美味的食物。”佩莉斯嘉不知道,埃迪塔是在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在这片不毛之地找到了足以救命的食物,但佩莉斯嘉知道,如果没有这些食物,她肯定活不下来。
每日每夜,妇女们都惨遭虱子叮咬,它们躲藏在每个接缝、角落、裂隙当中,它们繁殖得如此之快,以至于根本不可能根除。用食指和拇指抓住和捏碎虱子就足以耗费好几个小时。没有医疗护理,没有卫生条件,囚犯们总是忍不住抓挠虱子叮咬的伤口,而这会导致感染,经常足以致命。由于缺乏柔软的床铺,妇女们还会患上化脓的褥疮,她们的皮肤也会由于肮脏和营养不良而慢慢破损。
由于每间营房都塞进了多达800名妇女,无法遏止的疾病会侵袭她们毫无免疫力的身体,痢疾和腹泻都是她们经常承受的痛苦。所谓的盥洗设施就是一条长长的水槽,位于一处独立营房,两根水管喷溅出褐色脏水,盥洗室里也没有牙刷或肥皂。在营区待得最久的妇女,会向新人演示如何用沙土甚至粗砂擦洗自己,有些人还会用自己的尿来清洗褥疮。
妇女们每天只被允许使用一到两次营房厕所。所谓的厕所其实就是两条50米长的混凝土空心板梁,上面开了50个洞,下面是一条浅浅的沟槽。妇女们成群结队地被推进厕所,踏过泥泞的地面,走上粪迹斑斑的茅坑。她们只能上几分钟厕所,要么用手擦屁股,要么用床上肮脏的稻草,要么用衣服上撕下来的破布,别无选择。经期妇女也没有多少办法来吸干血迹。佩莉斯嘉倒是不用担心,只要她萎缩的身体里的胎儿还活着,她就不用担心这回事。
随着“继续走!”的叫声响起,妇女们就迅速走回营房,直到下一次点名。她们奋力地抬起脚,尽力让足以救命的鞋子不被贪婪的泥泞吸走。
每次妇女们放风时,佩莉斯嘉都会越来越绝望地左右扫视,祈求能看见她的丈夫。但是,她只能看见一排又一排营房上方数百座废弃不用的烟囱,还有许多被称为“鹳”的木制瞭望塔,以及从锅炉房里冒出来的滚滚油烟。
佩莉斯嘉开始明白,她对生存的希望幼稚得荒唐可笑。她正受到饥饿和口渴的折磨,因为褥疮而瘙痒难当,更难以忍受自己身上的味道,她几乎不敢相信她与蒂博尔被带离家后发生的一切。在这麻木不仁与恐惧不已的环境中,佩莉斯嘉说不定就像其他人那样,要么向毫无希望的命运屈服,要么就听天由命了。但在接连三次流产后,她却出人意料地决心活下来,而且要让孕育中的胎儿降临人世。她不知道别人会如何处置她,但无论如何,她希望能见丈夫最后一面。
男性囚犯住在远离比克瑙妇女营的地方,住在这个胡乱蔓延的复杂系统边缘地带的那些临时营房里。尽管有些穿着条纹囚服的男性囚犯偶尔来打扫厕所,或者到其他营区干些脏活累活,但这些来干活的男性囚犯通常佩戴粉红色三角徽章,这说明他们是同性恋者,所以佩莉斯嘉注定找不到她的丈夫。她开始担心,她那性情温和的作家兼银行职员的丈夫,可能早就“化作一缕青烟”了,或者已被运送到远方。随着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她的希望也日趋渺茫。

△一位德国军官站在一整车尸体前 资料图
在一天下午,她每天晚上向上帝所做的祈祷终于起了作用,上帝在她合眼之前回应了她的祈祷。透过带刺铁丝网的重重线圈,她突然发现蒂博尔混迹于一小群男性囚犯之中,正在通过她的营区。她马上认出了蒂博尔,尽管爱人看上去早已面目全非,他比过去更消瘦了,脸色苍白得如同透明。
佩莉斯嘉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冒着被射杀或被打死的危险,穿着木鞋走过泥泞、跨过电网,她小心翼翼地不去触碰电网,并且在被人发现之前对他说了几句话。
蒂博尔几周之前还与佩莉斯嘉共度30岁生日,现在看上去足足老了两倍。然而,当他看见“佩莉”,他还是欣喜若狂,他告诉佩莉斯嘉,他拼命祈祷,祈求佩莉斯嘉和两人的孩子能够活下来。他哭诉道:“正是这希望让我还活着!”
佩莉斯嘉告诉蒂博尔:“不要担心。我会回来的。我们能够做到的!”直到两人被迫分开,被拖回各自的区域,被擦碰得遍体鳞伤。
那天奇迹般地看见蒂博尔,知道丈夫还活着,这都给了佩莉斯嘉极大的鼓舞。再次见到蒂博尔,这个念头给了佩莉斯嘉极大的慰藉。蒂博尔鼓励的话语萦绕在佩莉斯嘉耳边,当晚她睡在埃迪塔与另一位妇女中间,她开始感觉到拯救孩子的强烈信心,当战争结束的时候,汉卡或米什科应该出生了吧?
就在佩莉斯嘉与蒂博尔被运走前夕,她们通过朋友的无线电台秘密收听到的新闻简报得知,战局已转而对德国人不利。法国已重获自由,美苏两国的盟军已接近会师。再过几个星期,她们就会获得解放,然后,佩莉斯嘉、蒂博尔还有两人尚未出生的儿子或女儿,就能回到家园,重拾他们被粗暴打断的生活。佩莉斯嘉把手掌平放在肚皮上,默默计算孩子降生的日期。佩莉斯嘉说:“我是在1944年7月13日怀孕的,所以我确切地知道,九个月何时期满。”
佩莉斯嘉的预产期是1945年4月12日。她把这个日期谨记于心,下定决心,无论如何都要保住这个婴儿,她会活下去,至少活到儿子或女儿降临人世。由于在战争头五年,她在布拉迪斯拉发基本上未受伤害,她现在还算健康,也还算健壮。她的丈夫还活着,她的丈夫深爱着她,还怀有生存的希望。
佩莉斯嘉曾经答应丈夫,他们能够做到,所以他们一定能够做到。
这是佩莉斯嘉日思夜想的美梦,直到1944年10月10日,一个晦暗不明的清晨,她终于梦碎。大约在她抵达奥斯维辛二号营-比克瑙灭绝营两周后,她与其他女囚犯再次被包围起来,三三两两地从门格勒医生面前走过,医生掌握着她们的生杀大权。医生面带笑容,擦得光亮的军靴上带着马刺,他随意挥挥马鞭,就选出了最为健康的女囚犯去服苦役。
与那些在隔离区或集中营里监禁数年的妇女相比,佩莉斯嘉依然双眼明亮、体态丰盈。她很快就被选中了。她甚至还没有明白过来,门格勒挥一挥手,她就被推向一边,与其他妇女一起被推向劳动队。
在分得一口面包以及一满勺汤以后,妇女们出人意料地再次被送上附近重载列车的货运车厢,列车已经在轨道上静静地恭候多时了。
当佩莉斯嘉默默饮泣,默念丈夫的名字,车厢门狠狠地关上,也把佩莉斯嘉再见到蒂博尔的美梦重重击碎。随着蒸汽机发出嘶嘶尖啸,巨大的黑色火车头把她拖离奥斯维辛的地狱之火,带她驶向新的、未知的终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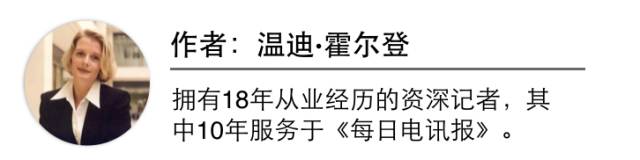

本文选自甲骨文丛书《天生幸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