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世界多么且新且旧。一半的小资产阶级是小农的,将家庭视为生存最核心的目标。另一半的小资产阶级想要分享他们幻想中贵族与大资产者的生活。人们探讨如何审查保姆的资质,如何更好地消费,必须得到与价签相配的服务,大众文化迷恋中国古代有仆人和成群妻妾的生活,迷恋英国庄园里管家的专业性。人们要车子,无穷无尽的口红,可供役使的、召之即来的肉体。

妾席
文 | 汤热海
1
一位这个时代的成功者,在游戏中赚了钱的人,资产百亿的富豪徐波,在微博上征女友,给出身高、性格、可以量化到十分制满分下的得分的美貌程度等等标准,说自己身边的女友知情(她是“7.5分”的女人),也不会介意。女人最大的价值是生育,他说,而他征女友,多多益善,要她们给他生更多孩子——现在他已经有两位固定女友和不少孩子了,母亲来源各异。他认为她们互不干扰,反正他一概不结婚,就不犯法,都是环绕在他身边的女人。
渐渐才明白为何古代言情小说更少苦情戏,即便有小风波,也缺乏现代爱情里常见的纠结心事,总是浪漫,总是美满结局——可以纳妾,这是古代言情小说的情节可以团圆多的“制度原因”。《玉娇梨》《定情人》,这些明清才子佳人小说里,张生无需遗弃崔莺莺。小姐活泼,主动,美丽,有诗才,与书生私定婚约结过良缘,书生便上京去赶考,金榜题名,由天子赐婚一位相府家小姐,或者又去上香郊游,将写了诗的纸扇委婉抛到又一位羞涩小姐身旁丫鬟的脚边,又一番两相倾慕定终身。也可以更简单,如《金云翘传》,姊妹同嫁一夫。姐姐历经磨折时,未婚夫先娶了妹妹,这是妹妹代姐姐把丈夫“守住”了,却正是姊妹情深的一柄明证,待姐姐归来,也与他成亲,皆大欢喜。
在《宛如约》这种将三位主人公的名字各拆一字拼成书名的才子佳人小说里,三位主人公是一男二女,一夫二妻;并不像《金瓶梅》、《林兰香》那些带着悲剧性写大家庭中的妻妾斗争与败落、美德之死的世情小说那样,书名是数位女主人公名字的集合。这些才子佳人故事恰恰是罗曼蒂克的、架空的、不现实的、写理想的、颂扬自由爱情的小说,倒总有两位太太。
最终总是一夫二妻大团圆。有的是两头大,两位都是正妻,都做夫人。有的是“验生辰分别尊卑”,按年纪分出妻妾,也正好姊妹相称一团和气。先后两位小姐,有些未曾谋面过,有些曾听闻对方诗才,一见面,执手相看,相互称羡,实在是男作者心中最美的一幅图画。这种设计,并不是把男人的见异思迁视作自然秉性,而是思甚至未曾迁移过,只是自然可以分割,见到新的女性,便自自然然地心甚爱之。而既然几位女子都有才德、愿主动追求爱情——都是那个时代的“先进女性”,怎么可能介意一夫二妻?平凡的正房,若是有德妇人,都会赞成丈夫纳妾,不然便会“耽妒妇恶名,伤夫妇和气”;这些女主角既是佳人,就在不会嫉妒埋怨之外,甚至连负面的情绪都不会有,并非“自当谅之”,而是真正能与其他女子相亲相爱,形如姊妹,其先进与能耐还在于可以如丈夫一般去真正欣赏那女子的才貌德行。男人哪里需要作什么痛苦选择,全部娶回家,才是有始有终,佳人皆欢。
《玉娇梨》的别名叫做《双美奇缘》。这标题正是这类故事的浓缩。数字为双,也大可以拓展到三,反正都是亲爱姐妹,虽然若拓到四五,就是《金瓶梅》、《林兰香》,更像小朝廷,要设计出奸臣,让皇帝——丈夫感到摆布不清,既劳且虑,更远于理想而靠近现实了。
历史学家史景迁写过《王氏之死》,重构了清初山东郯城贫苦农家一位妇女的逃亡历程。她裹着脚与人私奔,被丈夫抓回家后杀死,《郯城县志》和知县黄六鸿的回忆录记下了她的遭遇。这是贫贱版的潘金莲故事。杀妻故事很多,总是惩罚性的叙事,有武大郎这样的悲惨的男人与他们高扬正义的愤怒的兄弟,男人的嫉妒与愤怒与暴力可以理解,并不需要奥赛罗式的周折,将嫉妒表达为某个人性格中的软肋,一项固有弱点,而是男人理应愤怒。他们理应全部占有,彻底占有,充分占有,以多为善。而妇女则不应嫉妒——与丈夫的其他女子情同姐妹既是一种美德,也是一种妥善管理家务的才能,嫉妒者是无德、无才、无能的。
文学总是对神话的重写,理想沿着神话规定的欲望格栅展开。西方人重写奥德赛,安提戈涅,伊菲革尼亚在奥利斯。我们重写娥皇女英二女同嫁舜的故事。希腊神话里宙斯总在背叛他的王后,总出去四处留情,阿伽门农的妻子有了情人。而中国故事是妾的故事,是多妻的故事。一代代男文人继承着文明,继承着理想,妻妾成群是他们的天命,妻妾和平、子嗣众多是他们治家的才干与温厚的美德。女人则当如娥皇女英降下尊贵的心,实践妇道。
终其一生扮演娥皇和女英两姊妹的丈夫,这理想的社会角色是顺应天道的高贵。想一想,一夫一妻制度对于中国男人多么悲惨!多少男人怅惘着,张望着,心灵中总有缺口,等待妻妾成群。他们也是《会饮》中阿里斯托芬所描述的渴望着伴侣的人,本是一个,阴阳同体,却被分割成两半,整个生命都在寻找和等待完整。但这个男子等待的是他命定的另一半的许多女人。如不是许多,便构不成另一半。
一本《双合欢》的结尾,句子正如是。“金重一夫二妻,如英皇一般,只论姐妹,不分大小。鼓钟琴瑟,曲尽室家,鼓乐以谐老。故流风余韵,直传至今不朽。”
各俱风流佳话,正是最理想的美满家庭。一代代中国男人带着这团圆幻梦,成长到纳妾不再可以合法的二十世纪,而仍带着这幻梦。人走到哪里,权力与资本保证的社会地位上升到哪里,花名册就开到哪里。简直是一种中国式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2
如今公开纳妾是法律所禁止的了,而仍有实践中的多妻制度,仍有包养,仍有性买卖。儒家与资本结婚了,新儒家的特点恰恰就是支持传统,而不反对资本主义。女人被商业化的身体就像佃农理所应当用劳动换取教化与保护一样,是这种联姻中最情投意合的部分。接受澎湃新闻访谈时,学者戴锦华说:
今天中国的家庭想象和性别想象中,也依然深刻地存在着“多妻制”的幽灵。台湾学者张小虹曾经跟我说,台湾最热络的社会花边新闻、最受欢迎的电视剧,讲述的一定是“妻妾成群”的故事。其实大陆又何尝不是如此呢?《甄嬛传》是最典型的例子了吧?这样一部讲述“宫斗”的电视剧,却能唤起社会各个阶层的认同和喜爱,甚至主要是女性的欢迎。这充分说明那样一种多妻制的结构,依然存在于广大民众的心理中。
更重要的是,在今天的中国,资本已然召唤和复活了那个多妻制的幽灵。一个男性占有多少女性,是跟他占有的权力和资本成正比的。这里我想举一个电影的例子:娄烨的《浮城谜事》。那部影片的主人公——一个中产阶级中下层的男性——有一个合法婚姻所认定的核心家庭,同时还有一个以母亲为代表的中国血缘家庭,及权威所认可的事实上的“二房”,与此同时这个男人还在外面召妓,对象是一个来自贫穷家庭的女大学生。我当时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很震动,觉得娄烨捕捉到了中国社会现实中的某一种真实状态,即前现代的逻辑可以召唤出一种父权幽灵的权威性。
与“多妻制”在文化想象意义上的借尸还魂相比,更可怕、更具有腐蚀力的,是“多妻制”凭借权力和资本重新复活。事实上,资本结构本身就是父权制的;它一定是垄断的、暴戾的、贪婪的、实用性的、权威性的。垄断性资本作为一个大的父权结构,在全球建立的过程一定是个不断排除的过程,包括女性在内的所有弱势群体,注定处在一个不断被放逐和排斥的位置。
几乎可以预料到,几乎是非常必然地,又有新儒家学者在澎湃新闻撰文反驳,认为纳妾制度反而更能保护女性——认可妾与妾生子的地位是一种保护:
“如果经济地位一时无法平等,有些女性选择了依靠男人,甚至是与人分享,那么,给她们以合法地位,是不是更能关爱她们的价值与尊严?或者,在经济平等的前提下,如果几方自愿,一夫多妻的家庭被允许,是不是更能尊重人的权利和自由?”
脚下的这片土地有前现代的意识形态,其中掺杂着现代的、空洞的、陈腐的概念,但那些概念恰恰是对我们而言不再清晰透明,不再有力,甚至可笑,让我们不愿再不言自明地使用(“我们”是谁?类似于我的人)。而他们仍在使用(“他们”是谁?同床共枕的敌人,让人同情又想背过脸去),他们甚至认为他们的生活恰恰是对尊重、自由、公平这些概念的实践,与之相比,我们是伪善的。
在《王氏之死》描写的年代,买一个农家女孩做妻子需要三两银子,买一个美貌的妾要上百两,而若把当红妓女领回家则需要一千两银子。女孩都有价格,标定男人的幻梦近似于泡影的程度,获得——买到好货物是官场上商场中男人成功的标志,正如征服多位有诗才的追求自由爱情的女性是才子的能耐。徐波这样的人眼中看到的仍旧是这样的世界,我养她们,她们心甘情愿,两全其美,各取所需。B常去光顾如今靠微信传播广告的性服务,对我说,你不要觉得她们受压迫,漂亮,有钱,想做这行才做这行,可能一年只做几个月,很自由,我尊重她们,她们也尊重我,都是自愿的,哪里有压迫,更没有你想象的什么危险或者暴力——女孩有那么多类型,哪个男人若是想尝试暴力,大可以去找愿意接这种活儿的,何必强来。又说,非常安全,没有什么和警察有关的风险,也非常卫生,她们实际上比普通女孩子更注意。又说,我没有你想的那么经常去,要知道一次三千块。
除了价格和风险,还有什么能限制人?如果这被合理化为不仅正当而且自然的,如果市场上应有尽有。而风险也可以在价格的坐标中找到位置。《法国资产阶级史》中最重要的话恐怕是这一句,“资产阶级的座右铭:利润和安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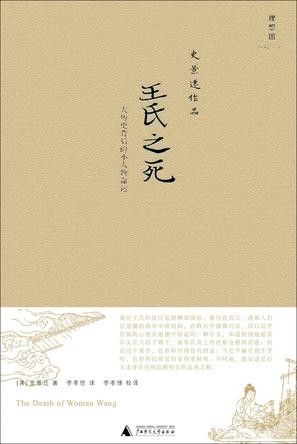
3
在《重负与神恩》中,薇依描写恶的特点之一是单调性。单调,不断复制地再次占有。恶不是像那些迷恋日式黑暗小说或中国式特稿的读者想象的那样,是丰富、有活力、不断更新、令人惊异的,它根本不是因为这些创造性内在的危险而为人所惧怕,而成为有颠覆性的力量。丰富、有活力、不断更新、令人惊异的,是善。恶是无聊、乏味、自我重复的,它只能追求更多——连环杀人犯不适合成为非虚构文学的主题,那实在是极其空洞无趣的。恶之恶在于单调。
她这样写,“恶的单调:无任何新的东西,在恶中一切全等值。无任何真实的东西,在恶中一切全是想象。 正由于这种单调性,数量才起到如此巨大的作用。拥有许多的女人(例如唐璜)或许多的男人(例如塞丽曼娜)等。恶注定具有这种虚假的无限性。这正是地狱所在。”
虚假的无限,资本的扩张,女人的重复(“找乖美女生宝宝”,要求:7分以上、23岁以下,乖,温柔,身材好;多么量化的标准,她们不同,她们完全相同,她们只是新的)。在恶中是没有爱的。我惊讶于徐波对普通人的说服逻辑:为什么要多生孩子?为什么不能独身?你会老的,孩子能养你。有一天你可能会瘫在床上,越多孩子越能照顾你。我这样穷,没有保障和财富,也并不健康,也不年轻了。而我同情这个有很多孩子的富人(多少人会因此觉得我愚蠢可怜!),为什么他总觉得自己会坠落,会有这些恐惧,会觉得人要把自己老年时的经济、瘫痪的可能性作为如今作出选择时的最重要的前提之一呢?早早为七十岁活着。
这样的恐惧或许是社会动荡和暴力的政治的结果,它否定爱的成分。最重要的始终是爱吧。我曾经写(我曾经想),体验过尊重的关系的人,不会再愿意回到控制的关系里去。现在我觉得这不是真的。人想和自己爱的人在一起。即使幻想被翻译成一个个噩梦,但"Without fantasy, there would be no love.” (“Desire/Love”, Lauren Berlant)。对吗?
性和身体的商业化、对女性的一再购买和复制,我对这些的厌恶已经非理性本身所能解释(真人偶状的充气娃娃?我根本不觉得那是什么亚文化)。这可能是我历史性的心灵结构,关于尘世中的爱我是阿里斯托芬的后人,向往排他的爱,有对唯一对象的求之不得感,仍旧相信人曾经是完整的球体而又被截成两半,在人世中孤零零地,血迹斑斑,无法滚动,需要另一半才能完整。
今天的世界多么且新且旧。一半的小资产阶级是小农的,将家庭视为生存最核心的目标,在这时不需要征引社会主义关于打破资产阶级核心家庭界限、靠近大同的那些理想,我会想要靠近《会饮》中苏格拉底的箴言,这世上有两种孕育,有母胎孕育与精神创生,有些人爱智胜过爱尿不湿。我会想,我的爱不仅植根在子女中,我的爱不需要植根在子女中,如果爱是对美的追求,它当具有某种普遍性。
另一半的小资产阶级想要分享他们幻想中贵族与大资产者的生活。在这时不需要征引乔治·佩雷克对巴黎人的嘲讽,你每一天都可以看到中产阶级在思考如何拥有上层的生活方式(上层的生活方式… 又是fantasy objects!不真实却统摄了人)。人们在微博上探讨如何审查保姆的资质,如何更好地消费,得到与价签相配的服务,大众文化迷恋中国古代有仆人和成群妻妾的生活,迷恋英国庄园里管家的专业性。
车子,无穷无尽的口红,可供役使的肉体:妓女、保姆、外卖快递员。在这种想象中“说来就来”的快速和商品以多为善的数量一样,极其重要,“说来就来”的价值不仅在于快——“方便”就像公平、自由一样,似乎是无可辩驳的价值,但是,“方便”究竟是什么意思?人们并不真的那么需要快,而外卖送餐以快为核心在电动车上贴出广告,它在送餐,但关键不在于美味,不在于卫生,而是“送啥都快”,“轻松下单,即刻到达”,“把世界送到你手中”,“送上门的美好生活”,这是一种承诺,保证随时无条件地呼应你的需要。实际上,“召之即来”的绝对服从与无需交流才是快的核心。当你想要他,他就上门。当你想要性行为,它就以金钱的中介迅速发生,约一个钟点。在与人有关时,我没有办法接受这样以即刻性(immediacy)为价值核心的构造,身体和性不仅是不应该被消费,而且不应该是“召之即来”的关系。微信上的性关系多么简单,以一套量化标准招募女性生孩子多么简单,call it, get it, immediately.
为什么即刻性这样重要?因为实际上他们什么都害怕,害怕改变,害怕恋爱,害怕冒险,一具不肯打开自我的身体,想要保证利润和安全。一本关于1870-1930年美国城市郊区历史的书有个相当有力的小标题,“第二章 布尔乔亚的恶梦:害怕几乎所有人和所有事”。整齐的城市郊区住宅区是山边绵羊成群、堂皇建筑旁引来湖水的英国庄园的现代平民版本,人们多么想要保住这绿荫,这整齐,这划一,这种可以传递到子女手上的田园诗生活。它并不坚实,一个黑人家庭做了邻居就可以“伤害”它,更别提金融危机或是大萧条。布尔乔亚的美梦是不断的增长和积累,是不改变。他们没有野心,也不爱冒险,服从科技、网络、新的交流方式后的资本爸爸,而当一点钱便可以让妓女、保姆、外卖快递员服从自己的需要时,有了帮手和下人,那种满足感无以言表,付钱,随时,随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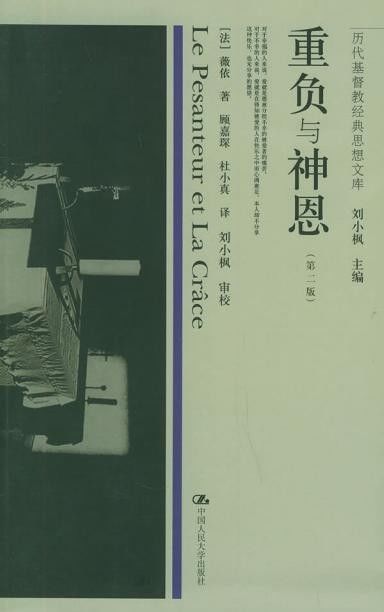
4
再次回到《重负与神恩》,让它帮助我们问出应当问的问题。“对任何一种行动,要从非事物的方面来看待,而不是从冲动方面来看待。不要问:为何目的?而是问:这由何处而来。 ”
在某程序员离婚后自杀事件中,应当问的问题不是,什么样的女人有蛇蝎心肠,要害男人的钱,以婚姻为得到财产的手段。这样的问题会导出:男人老实,女人坏;男人的财产应当属于自己的艰苦奋斗,而总要面临女性夺去的危险;女性是觊觎有钱男人、希求不劳而获的动物。这样的问题会导出以下问题:如何判断出哪些女人坏?如何更好地防范女人?怎样把财产牢牢抓在自己手里?——这个“自己”是个默认的老实而辛苦的男人,有些好色但仍旧真诚,好色这个弱点还更说明了他的软弱、真诚、老实。应当问的问题也不是,什么样的人会去世纪佳缘?而是问,为什么会出现“女性图财”的婚姻,是什么样的社会结构,什么样的不平等?财与貌为什么分别成为了性别化的资源?财与貌在什么条件下会成为相互交换、相互折价的资源?为什么它们可能成为婚姻被认为足够坚实的基础?另一条路径是少考虑性别问题,去问,交换是当代婚姻的内在条件之一吗?以什么交换什么,什么被商业化了?
实际上,某地高档住宅保姆纵火案后的大众情感,与某程序员自杀事件之后男性表现出来恐慌感,是有重合性的——“我得到了,但...... ”。
在经济学家罗斯高关于农村儿童早期发展问题的演讲后,应当问的问题不是,既然农村儿童缺少有质量的照料,那么谁该回家?即使是激进女权主义者所说的,“不如爸爸回家!”,“母亲在城市第三产业中实际上更容易找到工作”,这也是在指向如今在儿童哺育中只强调母亲作用的责任性别化的不平等状况,是在指向和批评其他问题,而不是对这个问题的正确提问。应当问的问题是,为什么农村儿童不得不与父母分离?为什么农村儿童在家乡无法得到有质量的照料与教育,只能够纯粹依靠家庭照料?国家与社会应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教育资源不平等,农村缺乏足够的、有质量的、价格可承担的照护机构和设施,缺乏相应的知识传播,制度建设,政策帮助。而责任只是在祖辈、母亲、父亲之间挪来挪去,批评总局限于或者是“农村祖辈的知识局限”,或者是“亲生母亲抛弃孩子外出务工”,或者是“父亲去哪儿了?” 历史地去看制度与政策变迁,会看到国家倡导生育、国家对下一代劳动力人口数量与素质的焦虑恰恰伴随着国家重新分配照料责任,将照料责任大幅度在城乡均转移给家庭,而在缺乏就业机会、营养条件、有治疗的照料设施与教育机构的农村,这个问题就更加严峻。
或者,应当问的问题很简单,他人正经受痛苦,这意味着什么?
鲁迅的《小杂感》是一缕缕语丝,一条条微博。他有时痛切,有时心冷,有时自我谴责,看到自己的麻木:“楼下一个男人病得要死,那间壁的一家唱着留声机;对面是弄孩子。楼上有两人狂笑;还有打牌声。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着她死去的母亲。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 ” 今人喜欢引他说的“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而实际上他写的是,“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将生活下去,我开始觉得自己更切实了,我有动作的欲望——但不久我又坠入了睡眠。”
如果将人的隔绝上升为一种深切失望后悲观的个人主义哲学,可以是《繁花》里,姝华见过下乡里的残酷和死亡后,写给沪生的信:“我写信过来,是想表明,我们的见解并不相同...... 人已经相隔千里,燕衔不去,雁飞不到,愁满天涯...... 年纪越长,越觉得孤独,是正常的,独立出生,独立去死。人和人,无法相通,人间的佳恶情态,已经不值一笑。人生是一次荒凉的旅行,我就写到这里,此信不必回了。 ”
而徐波所一再无力地强调的是——强调得这样猛烈,几乎像种下意识的自我反驳——他如今和未来的女友们,在妾席上,毫无疑问,一个个都非常幸福。
—— 完 ——
所有图片来自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