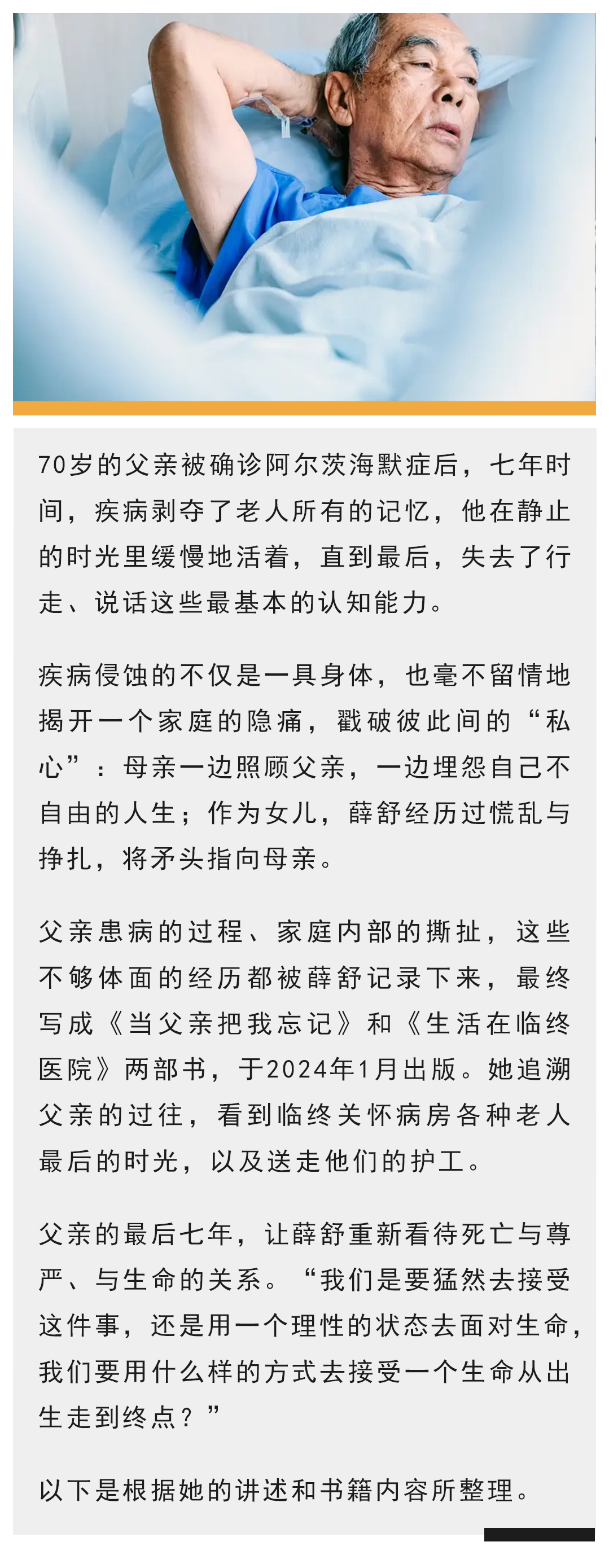
文 | 蔡家欣
编辑 | 王珊瑚
我原来的标题是《远去的人》和《太阳透过玻璃》,想尽量地用温暖、缓和的(方式)去呈现。当然,编辑更关照读者的需求,出版前换成两个更直观的标题,一个是《当父亲把我忘记》,第二个是《生活在临终医院》。有读者反馈,看到这个标题会出现想读、但是又怕读的心理。
这是我之前没有想到的。我们传统的教育更多是站在理想的、珍惜生活的教育这些方面,但在死亡教育这一块有匮乏,所以我们对死亡、对衰老是恐惧的。小时候,看见同学的父亲去世,我很恐惧,如果是我,我怎么能接受父亲没有了,这是小时候的一种逃避心理。
等到我父亲生病,我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上有老下有小,接受面对这件事情,特别困难。
2010年他的言行就开始出现异常。在桂林旅游,一位老头碰到我母亲的手,我父亲认定我母亲背叛他,生了半个月的气。我母亲退休后在一家饭店做财务,我父亲会突然出现在办公室的窗外查岗。当时,我和弟弟只是猜测是不是进入更年期,也可能是退休综合症?我们鼓动他去参加社区老人活动,报名老年大学。
那个时候,父亲时好时坏,还残留一点点记忆。他有过一段很无力的时候,跟我母亲吵架,他自己也很苦恼,我是这样的人吗?我感觉他知道(自己生病),但不愿意相信。
2012年,我父亲确诊阿尔茨海默症,记性越来越坏,做过的事转身就忘,他把一整袋核桃糕都扔进垃圾桶,自己一点都不记得,他忘记关煤气,自己走出家门,半夜我会接到我母亲的哭诉,我几乎天天要奔到父母那边。
每次到家之前,我会坐在车里缓一缓,想稍微喘口气,因为我知道,那是进去之后就没法再有笑容的一个地方。
我没有时间,也没法静下心来写小说。但我是一个写作者,不写东西会自责。某天晚上父亲已经睡了,我总算有了一点安静的时间,我想继续我的小说,当小说的题目出现在我的眼前,我的眼泪“哗”的一下就冒出来了,我做不了这个事情了。
我把所有的怨愤记了下来。我发现记录本身也是我的宣泄口,之后,我就开始回顾之前发生的事情,也记录下他每天的生病状况。写多了之后,我发现它其实是一个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的跟踪,我开始察觉到它的意义。
一位读者说,他父亲也得了这个病,处在半失控的状态,每天给初恋情人写信,而他母亲一边照顾老头,还要看这些信。他把这本书带给他母亲看,让她知道这是一个病,世上不是她一个人在遭遇这样的委屈。
因为这是非虚构,写的过程中,我时刻都在攻克产生的羞耻感。写小说,我可以用角色的身份,把人性的弱点、欲望暴露出来,躲在角色背后逃避被批评、被质疑。
但非虚构无处逃避。生病之前,无论如何,父亲都要表现出一个优雅的状态,生病后就不受控制了,本性里的那些东西就暴露了。比如,物质匮乏造成的缺乏安全感,极度节俭,以及从小离开家乡来上海谋生的超强警惕心。
他生病之后,我试图去理解他,他恐惧的是什么?最让他介意的、尊严受伤的东西是什么?这不是为了治愈他,而是要把它写下来,让我的创伤记忆得到一个疏解,这样你内心就不会再有羞愧感了。

●薛舒的非虚构作品。
最开始,我们要跟父亲那种狂躁的状态斗争,让他安静下来是第一要务。等到他真的安静下来以后,我发现他已经把我们忘记了。这个过程不是一两天,是好多日子积累起来的。比如到中期的时候,他知道自己有个儿子,却把眼前站着的、高大的男人当陌生人,要赶他走。
这个病就是这样,由近到远,慢慢忘了,忘到他小时候,最后把自己也忘了。很多人会说爸爸把你忘记了,这听起来很悲痛残酷。我总是羞于这么说,其实这是你过于爱自己了,如果你爱他,你就会觉得他把谁忘了都一样,他不会因为忘记你而痛苦。更重要的是,他处于那种与亲人隔绝的黑暗空间里,恐惧极了。
有一天,他认不出我了,把我当作他的老板,让我放他回去,不要一直困在这里上班。也许年轻的时候,他有过这样的工作状态,生存的问题实在太辛苦,或许也求过老板,给放两天假。我很心酸,不是为自己在他的记忆当中失去而心酸,而是为他在这样的状况下,依然处于一种困在上班的地方不能回家的绝望,最亲的人在旁边却感受不到,处于一种很悲苦的想象中。
后来,他忘记母亲,会突然对着母亲的背影叫“姆妈”。我的母亲本来计划工作到75岁退休。最开始,父亲还能走来走去,偶尔去买菜,这些都让她心存侥幸,他还是可以的。我和弟弟多次劝她辞去工作。她没有正面回复,每天早上准时去上班,好像并不担心她的老伴过得是否寂寞。我知道,她也在逃避,我没有权利要求她,那是她作为独立个体的选择。
坚持了四个月,她辞掉工作,比原计划提前了八年。母亲偶尔会感到委屈,坐在电视机前会忽然哭起来。我曾以为,母亲伺候父亲是不应该抱怨的,这也让我对她有一丝责备,因为她一度认为是父亲拖累了她,让她失去人身自由。
事实上,面对状况日益严重的父亲,母亲要忍受的更多的是情感上的痛苦,她将失去一个与她共同面对世界的人。
我从来不怀疑自己的孝心和责任心,也拒绝把父亲当一个孩子。他要求我讲他小时候的故事,好几次激动得要拥抱我,我一次次阻挡,我很难接受父亲像一个孩子一样,从我这个女儿身上寻求温暖的肌肤体验。
有一天,他在客厅与卧室之间移步,突然一屁股坐在地上,再不肯起来,他已经不会走路了。
2015年,我们把他送到医院的老年病房,每天有护工照顾他,我没有那么挣扎和焦虑了。五年时间,他不会说话,不会行动,不会与我们交流,就这么缓慢地活着,让我们在精神上感觉还被他需要。
有时候,我会想,他这么活着也挺好的。然而我又在反思,他自己不会表达,他如果会表达,他会告诉我什么,他想这么活着?还是不想?到底他的意愿是什么?这也关系到未来我会怎么想,当我不会表达自己的时候,我要怎么办?

●南京脑科医院的老年医学科里有个“水果”病区。病人平均年龄80岁,医护人员在病房前贴上各种水果图片,方便老人记忆。
父亲在老年病房住了五年。母亲每天都要去一趟医院,伺弄他吃饭,给他做一次全身清洁。父亲是7号床,眼睛经常看窗外,会发出“哎哟塞”的感慨。6号床双手被捆绑住,也会无意识地敲床栏,8号床气道狭窄,时刻都在打鼾。
大多数人都会认为病人很弱,有一些病人会以自己的弱欺负到你的强。比如,有一个老头,下半身经常包个尿不湿,女病人或者女护工进来,他就会掀开被子。他们躺到病床上,你无从想象他的过往,到底是良善或者非良善之人。
我在老年病房里面看到各种病人最后的时光。67岁的“小阿弟”中了风,每两个星期,他的女儿会买三两羊肉,切成小号麻将牌那样,蘸了调料,一块一块送进他嘴里。26号床的汪老太,总坐在走廊,向每个经过她的人讨要五角钱。9号床85岁的老头,儿子带来红烧肉,他一口气吃了四块,他儿子说,胃口这么好,病也会好得快,结果噎到了,洗碗的工夫就没气了。
护工们会把死亡叫“升天”。在老年病房,每个护工会负责一个病房,里面五、六个病人。
我经常会想起这些护工们。事实上,我不清楚她们到底叫什么,只知道是小彭、小张、小西……我父亲最后的一个护工小倪,踏实肯干,话也不多,她会把别人剩余的水果分给没有子女的老人吃。
还有小彭,有人“升天”了,她给其他病人耳朵塞棉花。72岁的肖老头是病房里唯一能跟小彭交流的病人。肖老头有三个儿子,每个月住院费、护工费都是三个人一起来签字,少一个,另外两个都不肯付钱。肖老头走的那天,小彭将一颗断齿塞进他的口腔,那是之前理发时,肖老头不小心咬到推子咬断的。
这些护工都是比较辛苦的那一拨人,不然她们也不愿意干这样的活,虽然收入高,也很熬人,每天一个病人68块钱,五个病人一个月大概能得1万多。
我在书里写到小丁的故事,她烫着酒红色小卷,又高又胖,力气很大,能双手托住病人一把抱起来。她说自己被家暴,丈夫拎着水壶往她头上浇,头皮都烫熟了。她离婚后又复婚,我很费解,小丁说,他打完又跪下来求我,我没办法。后来小丁被辞退了,她在操作室聊天,教新来的护工钻空子,被病人家属知道后投诉了。
医院就像一个村庄,护工、隔壁人家的事会传来传去,它就是一个熟人社会。护工之间挺惺惺相惜的,因为她们的处境都一样,24小时都生活在这里,要做点私事,又不能被监督的管理员看见,她们会相互掩护,这些都是特别生动的东西。我不觉得是偷奸耍滑,这才是人性,你要让她们释放一下。

●资料图。图源东方IC。
我总以为,父亲在病床上缓慢地活着,会活得很久很久。2020年新冠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他还是走了。我一直在想,当这一天来的时候,我要做什么?想到最后,我会归结到悼词。我想到的第一句话是:他从来知道自己是一个平凡的人。
最后没有悼词也没有告别仪式,我写了两本书。也许这也是父亲的愿望吧,他活着就很怕麻烦别人。
父亲的离开,对母亲的影响是一步一步,不是突然的。从父亲发病到失去沟通的能力,静静地躺在那里,我母亲已经接受了这样一个人的存在,或许在精神上他们已经完成了告别,肉体是最后的告别。我母亲是一个传统的中国劳动妇女,迎风接纳所有的命运,快乐也好,痛苦也好。最开始她也会有挣扎,但当她决定接受,她会安排好自己,好好地生活,这是生命力旺盛、强大的一个表现。
现在,她每天早上去打太极拳。她住浦东,我住浦西,每两个周末她会坐地铁到我这边来,我再开车送她回去。她有学习能力,网购看电视。她有一个明显的变化,以前家里重大的事情,她要让我父亲决定,自己不敢拿主意。现在她会自己拿主意,她也是在漫长的时间里去完成自立。
我们很少会去探讨死亡、生命这些问题。我曾经在她面前表态过,老妈,在你生活能自理的时候,你愿意自己生活可以,生活不能自理了,我请保姆阿姨在家里陪着你,或者住我这边,实在搞不定,去护理院也是必不可少的。
一开始,她会说我以后要么跟女儿住,要么跟儿子住,好像在揣度到底谁愿意接纳她?现在,她好像没有以前那么担忧,会说早晚得去养老院,这可能跟整个社会的认知或者宣传有关。
父亲经常在我的脑海里出现,我甚至觉得他都没有去世。他最后的5年时光都在医院里,不跟我们交流,我们只当他还存在。
从头到尾,我儿子看到我是怎么奔忙在这个事情中,有时我会跟他说,以后我老了就到护理院去,或者说以后有机器人,我买个机器人。我不要你陪伴在我身边,我不想用我自己的躯体来绑架你。我说这个话不是考验他,因为这个孩子是你的爱,你就要给他属于他的生活,不能用自己去绑架他。
阿尔茨海默症与普通病人最大的区别就是,他们无法带着爱和尊严走到生命最后一刻。现在我最不愿意说的就是给老年人尊严,当你家里有一个失智失能老人,谈尊严真的是一件特别奢侈的事情,我甚至觉得这是健康的、年轻的人的自我感动。对于正在面对衰老或死亡的这一拨人,我们谈尊严太高高在上了。很多老人身上插满管子,但他求生欲还在,你要选择什么?什么才是有尊严?
这很难取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