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雨,
苏州就成了姑苏。

月落乌啼,
寒山寺上钟声起;
留园清风,
陪君惊梦到三更。


姑苏的秋,
总带着些许的愁。
每每这时,
城里的人们就越发想念,
那个叫做“藏书”的地方,
和那碗羊汤的温度。

藏(cang)书所谓何地?
并非书店,
亦非图书馆,
而是苏州城西、太湖东岸的一个小镇
——“藏书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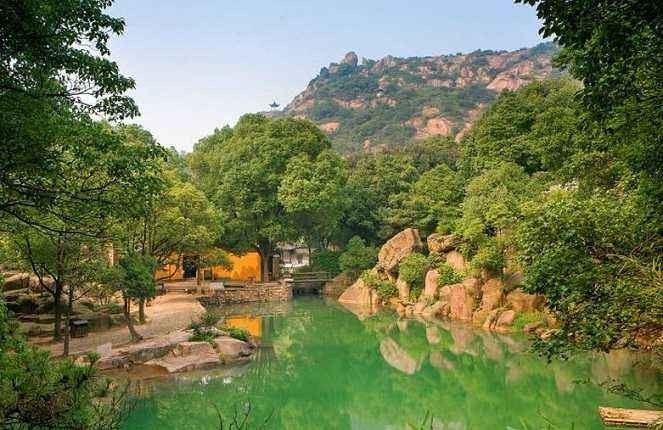
之所以叫作“藏书镇”,倒还真跟书有些联系。
还记得历史上那个“被离婚” 的朱买臣吗?买臣好读书,然妻子嫌他只读死书,不能赚钱,要把他的书全烧掉。
于是,买臣就把书藏于山中,偷偷拿出来读。后来他考取功名,人们为了纪念他,便把他的家乡命名为“藏书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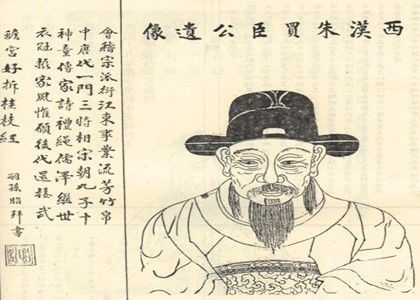
然而让这座小镇声名鹊起的,
并非这段勤勉读书的佳话,
而是这盆,
“鲜死人不偿命”的白汤羊肉。

只放盐,
不加任何辅料、调味料,
却不腥不腻、又清又鲜,
汤色乳白,
肉酥而不烂,
尽显羊肉之本味,
吃过之人皆赞久食不厌!

明、清时期,藏书镇境内群山绵延,水草丰厚,很适宜养羊,当地就有农民从事养羊、杀羊、烧羊、卖羊肉的行当。
一开始以担卖或摊卖为主,直到清末才在苏州城里开店经商,俗称“羊作”。
乡志记载,光绪22年,藏书周家场(今兴奋村)的周孝泉曾在苏州醋坊桥畔开设城内第一家堂吃的“升美斋”羊肉店。

一个不大的店面,
几张八仙桌,
几把方凳,
热情招呼的夫妻店家,
一盆热气滚腾的白汤羊肉。
几百年来,
这个场景都是冬日里的苏州人,
最最温暖的记忆。

“羊汤勿鲜勿要铜钿”。
藏书羊肉的魂儿,
全在一个“鲜”字。
而要想做到这个字,
除了考究的选材,
离不开独特的烹制方法。

一般选用放养爬坡的山羊,
以2岁左右的公羊最佳。
先将现杀山羊的胴体漂洗干净,
再将其切成4~6块放入盆堂。

盆堂,
不同于普通大锅,
而是用杉木做的木桶,
这是味道是否正宗的关键。
用木桶煮出来的肉汤,
汤更浓、味更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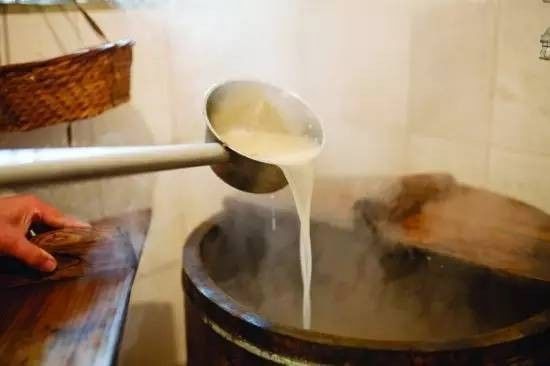
先急火烧沸,
待浮起一层浮沫后用勺撇去,
然后将盆堂中的羊肉取出,
放入冷水中漂清,
俗称“出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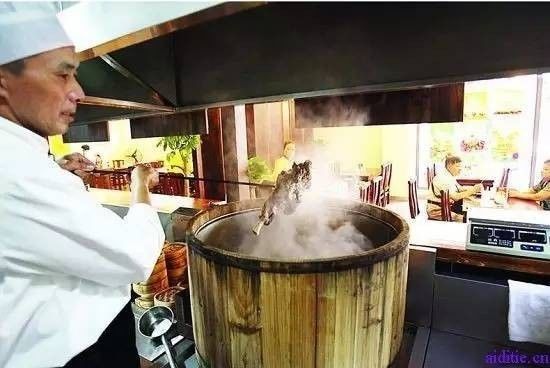
略待沉淀后,
将盆堂中的羊汤出锅,
盛入另一容器静置,
把锅底的沉渣清除,
称为“割脚”。

烹制过程中,还要注意不同羊肉放置的位置。
最下面放羊肉,上面是羊肚,而最上面则是鲜嫩的羊肝。急火烧沸后,便可将羊肝捞出,泡在淡盐水中,这样做出来的肝才不会变色变味。

“出水”、“割脚”之后,
把静置好的羊汤和出好水的羊肉,
重新倒入盆堂内,
旺火烧煮3小时以上。
其间大、中、小火都要拿捏得当,
待肉烂汤浓后,出锅拆骨,
放入竹制篮筐中沥水,
凉冻,以备切用。

滑爽的肉冻,
弹牙的肉皮,
鲜嫩的羊肉,
分明的层次感带给舌尖的,
却是极为复杂的味蕾刺激。

或夹起一块送入口中,
直接感受羊肉本身的鲜美;
或佐以蘸料,
让羊肉和酱汁充分碰撞,
产生更为奇妙的化学反应。

最后,
用一碗热乎乎的羊汤,
在全身毛孔的酣畅淋漓中,
结束这场、
回味无穷的味觉之旅。

苏州人好清淡,
最喜这一碗白汤的温存。
藏书羊肉却不满足于此,
在小小的羊身上,
下足了功夫。

秘制的红烧羊肉,
香气馥郁、肉皮锃亮
肥而不腻,入口即化,
口感比白切羊肉更为醇厚迷人。
羊膏纹理漂亮,
口感细腻肥美。


羊肚、羊鞭、羊腿、
羊肉水晶糕、清蒸羊肉、
羊肉芦粽···
白切、红烧、脆皮、爆炒···
智慧能干的藏书人,
甚至能用这羊肉,
做出4050种菜肴的“全羊宴”。


秋雨瑟瑟,
晚风来急,
加晚班回家的路上,
照例拖着疲惫的身子,
钻进一家藏书羊肉馆:
“老板,来一碗红烧羊肉面!”

吸一口劲道的面条,
咬一口酥烂的羊肉,
喝一勺鲜美的热汤,
整个身子便瞬间热乎起来。
恍惚间,竟觉得外面的风也小了,
雨也住了,
整个秋天,
都变得明朗起来。

人们都说,
藏书人是“一只木桶闯天下”。
红遍长三角的藏书羊肉,
一年消耗60万头羊,
全镇6500多人从事羊肉相关产业。
每年秋冬,
5000名外出的藏书人,
能带回5个亿。

然而对我们食客来说,
那些都不重要,
我们在乎的、
只是这一顿吃什么,
白切,还是红烧?
吃面,还是喝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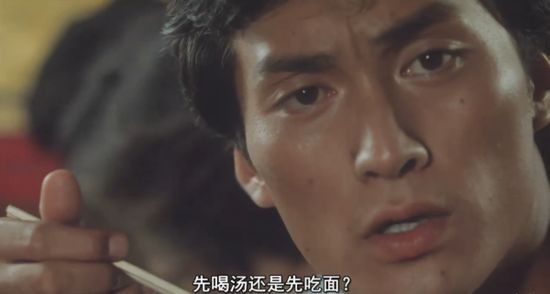
少年啊,
人生也有没有答案的时候。
只要能用食物,
自由地取悦自己,
就是最大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