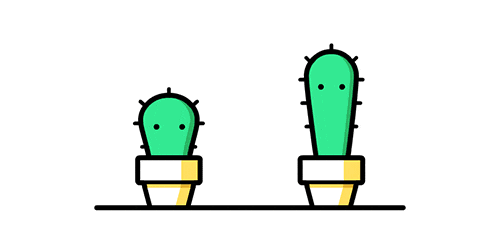巴金为什么要反复地修改《家》?
作者:宋剑华(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
在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中,巴金的长篇小说《家》,恐怕是修改次数最多的一部作品了。巴金对此并不讳言,他说“自从1931年和1932年小说在《时报》连载后,到1980年我一共修改了8次”。曾有学者通过校阅《家》的版本,发现“全集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对“开明本”(开明书店1933年版)做了14000余处删改,“几乎是每章、每段甚至每句都有所修改。”
巴金曾暗示说他的一些作品,“大的毛病是没法治好的了,小的还可以施行手术治疗。我一次一次地修改也无非想治好一些小疮小疤。”巴金此言大有深意,如果不去对读“开明本”和“全集本”,几乎无人知道《家》的“小疮小疤”与“大的毛病”,究竟是指哪些地方。我们不妨先来看看《家》中的“小疮小疤”。“开明本”语言累赘、病句颇多、欧化倾向严重,不仅为读者和研究者所诟病,就连巴金本人也不太满意;因此在“全集本”中,许多不规范的文字用语,他都做了必要的修正。此外,由于《家》的语言比较中性化,缺少四川特有的地域风格,倘若不是写着“成都”二字,无论是其中的人物还是景物,都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
1958年开始,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始陆续出版多卷本的茅盾、巴金等作家的文集。这属于现代文学“经典化”的规划之一。到1958年底,《巴金文集》已出版六卷。
然而,“大的毛病”就没有那么简单了。由于巴金在当初构思《家》的故事情节时,没有设计好时间背景、思想主题和人物性格等诸方面的逻辑关系,因此无论他后来怎样去修改,都力不从心、无法挽救了。所以,他后来才会萌生出“重写这本小说”的强烈冲动。《家》中到底有哪些“大的毛病”,是巴金挥之不去的内心隐痛呢?这也正是我要去揭开的一个秘密。
01
《家》的时间叙事与修改
《家》的时间叙事,是一个令人无法破解的谜。从表面观之,《家》是将高公馆内部所发生的一切悲剧,都集中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即1919年冬至1920年夏。理由很简单,《家》的开篇便描写雪片“飘舞”,正值腊月时节,觉民和觉慧从学校排练话剧《宝岛》后结伴回家。觉民还告诉琴一个好消息:“我们学校明年暑期要招女生了”,令琴立刻浮想联翩、激动不已。到了《家》的第二十五章,觉民又沮丧地对琴说,“现在这学期又快完了。招收女生的事简直没有一点消息。”“我们去年费了不少的工夫才把《宝岛》练熟习了。现在連上台的机会也没有,真是冤枉。”这说明《家》的时间叙事,的确是在半年之内。
那么我们又怎样去判断这半年时间,就一定是指1919年冬至1920年夏呢?同样是巴金本人告诉我们的。在“开明本”里,巴金只写觉慧坐在椅子上,读屠格涅夫的小说《前夜》;但是到了“全集本”里,巴金却特意加了一个注解:“《前夜》,屠格涅夫(1818—1883),沈颖译,这个译本本是1921年8月上海出版的,我在这里把它的出版提早了十个月的光景。”“提早了十个月”(从故事叙事本身来看,恐怕提早的还不止十个月),当然就是1920年了。1920年暑假觉慧离家出走,故此前那个冬天无疑就是1919年。
也许有人会提出疑问,《家》的时间叙事,不是交代得很清楚吗?为什么还会是个谜呢?我个人认为,如果真的相信这个说法,那将是大错特错了。巴金本人的时间观念是比较差的,他并不擅长时间记忆,但在《家》中他又特别爱去为“事件”标注“时间”,巴金所说的“大的毛病”,其实正在于此。比如“开明本”的第三章第一自然段,巴金让觉民这样对琴说:
“我们下学期就要读托尔斯太底《复活》,还有王尔德底《遗扇记》。《宝岛》已经读完了。”觉民对琴说,显出得意的微笑,这时候他们正走出了上房,刚下了台阶。“还有下学期我们底国文教员要改聘吴又陵,就是那个在《新青年》上发表《吃人的礼教》的文章的吴又陵!这真是一个好消息!”
到了“全集本”,巴金又修改为:
“我们这学期读完了《宝岛》,下学期就要读托尔斯泰的《复活》,”觉民对琴说,他的脸上现出得意的微笑,他们已经走出上房,刚下了石阶,向着他们的房间走去。“下学期我们国文教员要改聘吴又陵,就是那个在《新青年》上发表《吃人的礼教》的文章的。”
“全集本”删掉了王尔德的《遗扇记》,无疑是在纠正一个常识性错误,因为《遗扇记》原名为《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一共有三幕,由女翻译家沈性仁翻译并重新命名,在《新青年》杂志1918年12月第5卷第6号和1919年第6卷第1、3号上连载。由于巴金意识到那个时期的《新青年》,在成都还没有流行起来,人们还不可能知道王尔德和《遗扇记》,故将其删去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接着问题又来了,托尔斯泰的《复活》,1922年才由耿济之翻译,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1919至1920年,人们根本就看不到中文版的《复活》,于是巴金便让觉慧去读英文版。在“开明本”中,觉慧“把民哥新买来的英文版《复活》翻开读了十几页”,但是到了“全集本”,却改成觉慧一口气“读了几十页”。我们姑且不说那个时代,在成都能否买到英文版的《复活》,觉慧只是一个“外专”二年级的在读生,他真有那种阅读原文的外语水平吗?
我个人对此是深表怀疑的。最令人大跌眼镜的,还是巴金对于历史的无知,这绝不是我危言耸听,而是一个白纸黑字的客观事实。比如,《家》的时间叙事,既然被限定为1919冬至1920年夏,那么他为什么要让觉民去“穿越”,一下子又回到了1918年上半年呢?吴虞任教成都“外专”,是1918年秋季的事情,关于这一点,《吴虞日记》里有记载。况且吴虞文章的题目是《吃人与礼教》,而不是《吃人的礼教》,发表在1919年11月《新青年》第6卷第6号上,也被前移了一年多时间。
如果巴金聪明的话,根本就不提吴虞,换一个所谓的“新派人物”问题就解决了,这样也不会让人抓住把柄。可他偏偏要把《家》的故事叙事,与时代大背景联系起来,自己为自己挖了一个跳不出来的“大坑”,所以才为《家》留下了无穷的隐患。即使巴金后来发现了这些“大的毛病”,他在“全集本”里也无法去做全面修改了,因为这将意味着整部作品的情节结构,都要被彻底推翻并重新去进行设计。从1919年冬退回到了1918年初,究竟哪一个时间才是故事发生的真实时间呢?恐怕连巴金自己也搞不清楚了。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巴金之所以反对把“开明本”纳入新文学大系,实在是因为时间叙事太乱了,乱得连他自己都不忍卒读,又怎能让后人承认它的经典地位呢?时间叙事的混乱性,必然又会直接影响到历史叙事的混乱性,这是我在对读“开明本”与“全集本”时,印象最深的一点感受。比如,《家》告诉读者觉慧和同学们闹“学潮”,起因是十几个军阀士兵,搅乱了《终身大事》的演出现场,并且还打伤了许多学生。对此,“开明本”第八章第十自然段是这样描写的:
到了里面他们坐下来,乱叫好,乱闹,比在普通戏园里还要放纵。……有的甚至于跑到戏台上去把演女主角的抱着乱亲嘴。我们和他们打起来,乱子闹大了。
我个人感兴趣的不是学生和士兵打架,而是男女生同台演出《终身大事》。《终身大事》是胡适写的一个话剧剧本,发表于1919年3月《新青年》杂志第6卷第3号。胡适说这部话剧原本是用英文写的,“后来因为有一个女学堂要排这戏,所以我又把它翻成中文。”未曾想“因为这戏里的田女士跟人跑了……竟没有人敢扮演田女士”,《终身大事》的演出也就再无下文了。直到1924年,《终身大事》才由洪琛担任导演,在上海第一次正式演出,了结了胡适的一桩心愿。
令人感到莫名其妙的是,《终身大事》当时在北京都没有人敢演,巴金不仅让其在成都公开上演,而且还是男女生同台演出,这真是一个天大的笑话。到了“全集本”,尽管巴金将“把演女主角的抱着乱亲嘴”一句删掉了,然而他却并没有删掉演出《终身大事》这件事,历史叙事错误仍然存在。我为此感到很纳闷,巴金既然反复地修改《家》,那么他完全可以换一出剧目,以消除这个不该出现的人为疏忽,干嘛非要死盯着《终身大事》不放呢?答案只能有一个,即他根本就不了解《终身大事》的冷遇真相。
由时间叙事的混乱性,再延伸到历史叙事的混乱性,这便是作为现代文学经典的《家》,始终都难以消除的巨大缺憾。只有找到了这些“大的毛病”,我们才能理解巴金为什么要反复地修改《家》——因为一部文学经典,是不能留有明显瑕疵的。
02
《家》的思想叙事与修改
若问《家》的创作主题是什么,人们会异口同声地回答道:暴露封建“礼教”和“大家庭”的“吃人”罪恶。巴金自己也一再声称,他写《家》的目的,就是要“我控诉”。即使到了1980年以后,他仍坚持这种信念:“那十几年的生活是多么可怕的梦魇!我读着线装书,坐在礼教的监牢里,眼看着许多人在那里面挣扎、受苦,没有青春,没有幸福,永远做不必要的牺牲品,最后终于得着灭亡的命运。还不说我自己所身受到的痛苦!……那十几年里面我已经用眼泪埋葬了不少尸首,那些都是不必要的牺牲者,完全是被陈腐的封建道德、传统观念和两三个人的一时的任性杀死的。我离开旧家庭,就像甩掉一个可怕的阴影,我没有一点留恋。”
对于巴金这番慷慨陈词,我曾高山仰止、深表敬意,但自从对读了“开明本”和“全集本”,我个人的看法却发生了很大变化。因为近十年来,新文学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正是我的研究重点。我查阅了几乎所有的权威性词典,都没有收录“礼教”这一词条;唯一收录“礼教”词条的《汉语大词典》,也只说“礼教”乃是中国传统的“礼仪教化”。权威性词典一般都是由著名学者集体编撰而成,他们对于“礼教”一词应该是再熟悉不过了,可为什么却对其视而不见、缄口不言呢?答案恐怕只有一个,那就是“礼教”作为一种宗教式的文化概念,在中国历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既然“礼教”的概念难以成立,那么巴金在《家》中所反的“礼教”,又是指向那些具体内容呢?无非就是长幼有序的等级观念。比如巴金在《家》中一再强调说,高老太爷是一家之尊,他的话就是命令,任何人都只有服从不能反抗。可是通过阅读《家》,我认为巴金对于所谓“礼教”,其实并不十分熟悉。举一个例子,在《家》的第十五章里,巴金这样去描写高家过年的祭拜仪式:
依然是由祖父开始向祖先叩了头。祖父叩了头就进去了。接着是觉新底继母,其次是三叔克明,再其次是三婶张氏,这样下去,五婶之后又是陈姨太……。
拜完祖先之后,便是高家儿孙叩拜长辈高老太爷:
于是叫了仆人取开了拜垫,单铺着红毡,克明又进去请了祖父出来,先是克字辈的男男女女围着他跪下去叩头请安,然后是觉字辈和淑字辈的孙儿孙女给他拜贺。他带着笑满意地受了礼,便走进自己屋里去了。
这一场景设计令人疑窦丛生:陈姨太在高家,究竟是何种身份?巴金曾坦承,“我写《家》的时候,我恨陈姨太这个人。……我在陈姨太身上增加了一些叫人厌恶的东西。但即使是这样,我仍然不能说陈姨太就是一个‘丧尽天良的坏女人。她没有理由一定要害死瑞珏,即使因为妒忌。陈姨太平日所作所为,‘无非提防别人,保护自己。因为她出身贫贱,并不识字,而且处在小老婆的地位,始终受人轻视。”巴金“恨”陈姨太我们可以理解,但总不能因为“恨”就乱了辈分吧?
电视剧版《家》部分演员合影
“开明本”的第九章,并没有明确交代陈姨太在高家的身份,只是说“祖父还有一个姨太太……和祖父在一起过了十多年”。仅从这段文字表述中,读者并不知道陈姨太是在祖母生前还是在她去世以后,才被高老太爷就娶回家的,故巴金称她是“姨太太”或“小老婆”,人们很难提出异议。但是到了“全集本”,巴金却把她改坏了,他说“祖父还有一个姨太太……她是在祖母去世以后买来服侍祖父的”。既然陈姨太是在祖母去世后才进门的,那么她无论是“娶”是“买”(“开明本”里并没有说是“买来”的),都应被视为是续弦;而续弦又是继母的身份,是不能用“姨太太”或“小老婆”去称呼她的,更不能让其排在儿媳们之后去给高家的祖宗磕头。
还有,《礼记》曰“继母如母”,陈姨太既然是继母,她就理应同高老太爷一道去接受儿孙们的贺拜,但巴金却偏偏不这样做。与之相反,觉新兄弟的继母周氏也是续弦,为什么不被称为“周姨太”呢?我说巴金未见得真懂礼教,这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据。五四新文学作家在这一方面,明显要比巴金强得多。比如彭家煌的小说《节妇》,也是描写了一个叫阿银的丫头,被卖给了郑老太爷做续弦;但在郑老太爷死后,他的儿孙起码在表面上遵循礼制,照样承认她的长辈身份——比她大二十多岁的儿子称其为“亲姆”,与她同龄的孙子也得叫她“太婆”。由此可见,“恨”与反“礼教”都不是借口,“不懂”才是导致高家辈分错乱的根源所在。
《家》要暴露“礼教”和“大家庭”的罪恶,就必然要把批判的矛头指向那个“万恶之源”的高老太爷。不过在“开明本”中,巴金对高老太爷着墨不多,写得也并不是那么“坏”,很难激发起读者“恨”他的情感。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曾有读者对巴金把高老太爷写得不够“坏”而心存不满,特别是作者最后让高老太爷彻底醒悟了,他们深感遗憾且表示完全不能够理解。巴金本人也发现了这一问题,所以在“全集本”里,有关高老太爷的叙事部分,基本上都做了修改。首先是将“开明本”中的“祖父”称谓,全都改成了“高老太爷”;接着又将高老太爷的形象,做了“丑化”和“去亲情化”地艺术处理。而改动最大的地方,则是将鸣凤“送人”和觉民的“婚事”。
话剧版《家》剧照
鸣凤以死去抗拒做冯乐山的姨太太,这无疑是小说《家》的一大看点;因为它最能揭示高老太爷的残忍性格,巴金当然将其视为是得意之笔。然而,在“开明本”与“全集本”中,鸣凤之死是否与高老太爷有关,前后竟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说法。比如在“开明本”的第十六章,鸣凤这样对觉慧说:
“老太爷底一个朋友姓冯的要讨姨太太,冯老太太也常常到我们公馆里来玩,她看中了我和婉儿,要选一个去,听说已经来说过了。婉儿从四太太那里听到一点风声,她就来告诉我。若问我们底主意,你刚才已经听见了。”
鸣凤说得很清楚,冯家要娶高家的丫环做姨太太,是冯老太太与四太太(克安的老婆)两人的主意,高老太爷并没有参与其中。可是到了“全集本”里,情形就完全变了:
“冯老太爷要讨姨太太, 冯老太太也到我们公馆里头来过, 她说, 我们公馆里的丫头都长得不错, 向老太爷要一个。听说老太爷想在大房同三房的丫头中间挑一个送去。婉儿从三太太那里听到一点风声, 她就来告诉我。若问我们的主意, 你刚才已经听见了。”
这样一改, 高老太爷自然就变成了杀害鸣凤的罪魁祸首。这件事我始终都没有弄明白:冯乐山要讨姨太太,其妻冯老太太不但不反对,反而还亲自出马去牵线搭桥,这符合人之常情吗?我们再来看看觉民的“抗婚”。觉民反对同冯乐山的侄女结亲, 用逃跑的方式和祖父对抗,高老太爷当然很生气;这至多说明他人老了,性格有些固执,与“虐杀”儿孙之罪名何干?在“开明本”的第三十五章, 巴金让高老太爷临终时幡然醒悟:
“我错了,我对不起他。……你快去叫他回来罢,我想见他一面。……你给我把他找回来,我绝不会再为难他的……”祖父说到这里用手拭了拭眼睛,忽然看见觉慧底眼泪正沿着面颊流着,便感动地说:“你哭了。……你很好……不要哭, 我底病马上就会好的。……你要好好地读书,好好地做人……这样就是我死了, 我在九泉也会高兴的。”
后来巴金觉得这样写过于亲情化了, 不利于突出《家》的反封建主题:所以到了“全集本”里, 他又改为道:
“我……我的脾气……现在我不发气了……我想看见他, 你把他喊回来。……我不再……”祖父说, 他从被里伸出右手来, 揩了揩眼泪。……“你快去把你二哥喊回来。……冯家的亲事……暂时不提。”
“暂时不提”也许以后还会提,巴金在“全集本”里,为高老太爷留下了一个可以反悔的伏笔;但“我错了”则不同,在“开明本”里他知错就改,立刻让觉新退掉了这门婚事。实际上,“开明本”已经流露出了觉慧同爷爷和解的明显意图,比如觉慧望着重病在床的爷爷,“他想着许多年来只有这一天,而且在那短时间内,他才找着一个祖父,一个喜欢他的祖父,而且他们两个才开始走向着相互了解的路。”但是到了“全集本”里,却被改为“看见祖父痛苦地抽气的样子,他便明白现在的确是太迟了。”这一改,便彻底杜绝了新旧两代人之间的和解希望——提升反封建的思想主题,其代价就是家庭亲情的被消解。
话剧版《家》剧照
03
《家》的人物叙事与修改
核心人物的大幅度修改, 是《家》的自我经典化过程的一个重要因素。对读“开明本”与“全集本”, 我发现《家》中的主要人物,其形象和语言都有所改动, 有的甚至是脱胎换骨、判若两人了。毋庸置疑,《家》中的人物修改,完全是服从于反封建的思想主题;所以人物形象的模式化痕迹, 也越来越明显。
鸣凤形象的修改, 主要是身份错位的修改。在“开明本”中, 鸣凤是一个纯洁可爱的“美”的化身, 在她身上不仅倾注了青年巴金的全部情感, 同时也是他攻击“礼教”和“大家庭”罪恶的精神动力。巴金笔下的鸣凤, 知书达理、含情脉脉、文静典雅、举止得体, 与其说她是个丫环, 还不如说她是个小姐。巴金说他写这一人物, “并没有一点夸张”, 鸣凤的一切甚至包括投湖自尽, 都是由“性格、教养、环境”所决定的。 “性格”无疑是与生俱来的, 而“教养”和“环境”则是指大小姐在世时, 教她认字和人生影响。比如在第十章里, 巴金让鸣凤对觉慧表白道:
“以前大小姐向我讲过爱字, 后来琴小姐也同我讲过, 直到近来我才知道爱是怎么的一回事。我每一想到你, 或者看见你, 似乎天大的痛苦也可以忍下去了。你不晓得你帮助我忍受了不少的痛苦。我常常在心里暗暗叫着你底名字, 然而在人前我却不敢叫出来。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地感激你。”
电视剧版《家》中的鸣凤和觉慧
这种叙述方式很有意思:鸣凤“自由恋爱”的现代意识, 是经大小姐思想启蒙而得来的;可是大小姐在五四以前就死了, 那么她又是从哪儿获得的现代意识呢?如果追问下去,这种叙述方式很有意思:鸣凤“自由恋爱”的现代意识, 是经大小姐思想启蒙而得来的;可是大小姐在五四以前就死了, 那么她又是从哪儿获得的现代意识呢?如果追问下去,则只能是中国古代的言情小说了。
《家》让鸣凤和觉慧两人, 打破了主仆之间的身份界限, 在精神与人格平等的基础上相爱, 固然具有反传统的积极意义;但是让一个丫环, 去负载一个小姐的思想情感, 并以此去挑战封建等级观念, 则完全是有失生活真实的。想必巴金自己也觉得有些不妥, 故他在“全集本”里删改道:“我只要想到你, 看见你, 天大的苦也可以忍下去。我常常在心里暗暗地喊你的名字, 在人前我却不敢喊出来。”
“全集本”去掉了一个“爱”字, 表明鸣凤知道自己的出身微贱, 她与觉慧两人的关系, 是不可能有什么结果的;故用心“恋”去保持一定的距离, 把“爱”表现得委婉而含蓄, 虽然并没有改变身份不对称的爱情叙事结构, 起码令人感到还可以接受。另外, 在“开明本”的这一章里, 当觉慧说要娶鸣凤做三少奶奶时, 她惊喜之余的那番感叹, 更不符合一个丫环的口吻:“有一两次我仿佛看见你底面颜不住向空中升上去, 愈过愈高, 对于我好像变成了一个高得不能够摘取的月亮。那时候我禁不住要想, ‘这不过是一场梦罢了’。我以为我这一辈子是没有望的了”。
像这一类诗情画意的抒情性语句, 在“开明本”里还有很多。比如在第二十六章里鸣凤投湖之前,长篇大论地去诘问“我底生存究竟是这样渺小吗”的哲学问题等等, “全集本”不是做了全删, 便是做了改写。即便是如此, “全集本”中的鸣凤形象,仍有身份错位之嫌, 尽管巴金在“全集本”中, 试图用一句“她一点也不像丫头”去搪塞;可是“不像”丫头, 她毕竟还是丫头啊。
电视剧版《家》中的鸣凤和觉慧
在“全集本”里, 觉慧的形象变化最大, 几乎大部分文字置换, 基本上都与他有关。“开明本”最初描写他反抗家庭, 多是一种青春期的叛逆现象。巴金自己也承认, “他不是一个英雄, 他很幼稚。” 比如第十九章, 觉慧和兄弟姐妹们一起划船赏月, 淑英吹笛, 觉新吹箫, 其他人跟着唱歌, 大家都很快乐,只有觉慧一人感到孤独:“第一他不会唱歌, 第二他对于音乐完全是外行。”这恰好说明了一个问题:觉慧除了“思想”, 其他一窍不通;因缺少“知音”而厌恶“家”, 应是他躁动叛逆的主要原因。“全集本”则不同, 巴金把一个原本是属于青春期的叛逆少年, 打造成一个具有现代人文精神的五四青年, 觉慧的形象早已是今非昔比了。“全集本”对于觉慧形象的重新塑造, 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大的方面:
从““幼稚”到“成熟”。“开明本”里的觉慧, 其所谓的反抗叛逆, 与他的年龄和阅历, 构成了正比例的关系。他还没有踏入社会, 尽管有《新青年》和《新潮》的思想启蒙,必定还不了解社会人生的复杂性;所以他经常会茫然无措, 甚至于徘徊动摇, 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从““虚浮”到“真诚”。觉慧与鸣凤的爱情叙事, 历来都被学界所津津乐道, 认为他敢于打破主仆之间的身份界限, 去大胆追求一个出身卑贱的丫环, 其反“封建礼教”的现代意识, “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 。这种结论, 无疑是源自于对“全集本”的阅读感觉。
实际上, 巴金要比我们的头脑清醒, 觉慧只不过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他虽然情窦初开, 却并不知道什么是爱情;因此在“开明本”里, 巴金只描写了觉慧的青春期躁动, 同时也指出了他在处理同鸣凤的关系时, 那种不成熟的人格缺陷。比如觉慧说鸣凤“你真纯洁, 你真伟大!我比起你底一只脚也不配呵。”他甚至还对鸣凤发誓, “到那时我会告诉太太我要娶你。”至于鸣凤如何“伟大”, 他为何一定要娶她, 其实觉慧自己也不清楚。正是因为觉慧对鸣凤的“爱”, 带有极大的盲目性;所以后来一旦遇到了阻力, 他便“准备着到了某个时候便放弃她”。
从““动摇”到“坚定”。我个人始终认为, “开明本”中的祖孙关系, 处理得要比“全集本”恰当, 尽管巴金对高老太爷极为反感, 但却并没有完全切断觉慧和爷爷之间的血脉亲情。其实在“开明本”的第九章, 巴金就已经做了明确地暗示, 觉慧完全是有可能同爷爷和解的:
祖父对于他简直成了一个谜, 一个神奇的谜。但他对于祖父依然保持着从前的敬爱, 因为这敬爱在他底脑里是根深蒂固了。儿子应该敬爱父亲, 幼辈应该敬爱长辈——他自小就受着这样的教育, 印象太深了, 很难摆脱, 况且有许多人告诉过他, 全靠他底 (的) 祖父当初赤手空拳造就了这一份家业, 他们如今才得过着舒服的日子;饮水思源, 他就不得不感激他底祖父。
电影版《家》中的高老太爷
因此, 到了第三十五章, 觉慧面对着奄奄一息的祖父, 感到了深深地内疚:“事实上如果早一天, 如果在还没有给过他一线希望的时候, 那么这分别并不是什么难堪的事, 他决不会有什么遗憾。然而如今在他底面前躺卧着那垂死的老人。他在几点钟以前曾经把他底心剖析给他看过的, 而且说过自己是怎样错误的话。”毫无疑问, 祖父已经承认了他的错误, 并将心“剖析给他看过”;可是觉慧却没有在祖父生前, 主动地向他敞开心扉并做忏悔, 这才是令觉慧感到“难堪”和“遗憾”的心灵之痛。形而上反“家”与形而下爱“家”, 觉慧深陷于这种矛盾之中不能自拔, 巴金意识到这将动摇他攻击“大家庭”的顽强意志, 同时也会颠覆《家》的反封建主题。因此在“全集本”里, 巴金把这些段落全部都删掉了, 只留下这样几行轻描淡写的文字:
“太晏了!”这三个字沉重地打在觉慧的头上。他几乎不懂得这个“太晏了”的意思。但是看见祖父痛苦地抽气的样子, 他便明白现在的确是太迟了。他们将永远怀着隔膜, 怀着祖孙两代的隔膜而分别了。
仅从修改后的这几行文字中, 读者已经很难看出觉慧有什么“难堪”与“遗憾”了;巴金让他们祖孙二人带着“隔膜”诀别, 即实现了《家》的“去亲情化”叙事, 又强化了觉慧作为一个五四青年的存在意义——“全集本”《家》的启蒙诉求, 也最终得以确立。
对读了《家》的“开明本”和“全集本”, 我个人对于这部文学作品感受颇深。时间叙事、思想叙事和人物叙事的混乱性, 足以说明巴金在创作《家》的初期,并没有做好必要的思想准备, 诚如陈思和所指出的那样:巴金“不是对整部小说有了详细的构思以后才动笔的, 而是确定一个大致的主题就顺着灵感写下去”;如果不是得到了自己大哥的死讯, “难保《家》不会以另一种面貌出现。” 这真是醍醐灌顶的金玉良言。一部缺少缜密构思的艺术作品, 自然会留下许多“大的毛病”;那么《家》的经典性, 也将重新去接受历史的检验。
原载于《南方文坛》